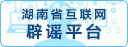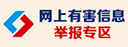沈從文的醴瓷情結(jié)
李維善
我認(rèn)識(shí)沈從文是從1959年1月開(kāi)始的,。1959年1月我在北京,,參加為研究慶祝新中國(guó)成立10周年而興建的人民大會(huì)堂等十大建筑內(nèi)部裝飾的會(huì)議,。在那次會(huì)上,醴陵瓷業(yè)承擔(dān)了人民大會(huì)堂,、歷史博物館、解放軍博物館,、民族文化宮,、工人體育場(chǎng)等幾大建筑的日用瓷、藝術(shù)瓷的光榮任務(wù),。為了使醴陵瓷更好地貢獻(xiàn)給首都人民,,我決定趁在京的機(jī)會(huì)拜訪一些老專(zhuān)家以求指點(diǎn)。沈老那時(shí)在故宮工作,他對(duì)我國(guó)陶瓷有獨(dú)特的研究,,他是湖南人,,又是很有名氣的大作家,我決定先去拜訪他,。同去的有當(dāng)時(shí)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畫(huà)師唐漢初老藝人,。沈是一位大名人,我們第一次見(jiàn)面,,事先又沒(méi)有打招呼,,不免有些唐突。打聽(tīng)了路線(xiàn)后,,經(jīng)過(guò)東堂子胡同到了51號(hào)就冒冒失失地進(jìn)了他的家門(mén),。沈聽(tīng)說(shuō)我們是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年輕的所長(zhǎng)(我那時(shí)30歲)和繪瓷的老藝人,二話(huà)沒(méi)說(shuō)立即丟下了手頭的工作(當(dāng)時(shí)正在伏案寫(xiě)東西),,特別熱情地接待了我們,。

進(jìn)門(mén)后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沈老家靠墻的一面是四個(gè)滿(mǎn)滿(mǎn)當(dāng)當(dāng)?shù)臅?shū)柜,,柜子上疊滿(mǎn)了他收購(gòu)的古瓷,,書(shū)桌上攤滿(mǎn)了他的稿件。一個(gè)文化人的氛圍呈現(xiàn)在眼前,。那天正是星期天(1月20日),,說(shuō)明沈老是很繁忙的。那次見(jiàn)面談的家長(zhǎng)里短全是瓷器的事,。沈老生前沒(méi)有到過(guò)醴陵,,但這次談話(huà)中他問(wèn)起了醴陵的釉下彩,還談了醴陵瓷器的其他事,,似乎對(duì)醴陵瓷業(yè)有一定的感情,。后來(lái)我們才知道,原來(lái)開(kāi)創(chuàng)醴陵釉下細(xì)瓷的清光緒進(jìn)士,、翰林院翰林,、鳳凰人熊希齡(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前身——湖南瓷業(yè)公司和湖南瓷業(yè)學(xué)堂的創(chuàng)始人,首任民國(guó)國(guó)務(wù)總理)就是他的姨父,。當(dāng)說(shuō)到我們這次進(jìn)京是參加十大建筑內(nèi)部裝飾的會(huì)議時(shí),,他說(shuō)他知道有這個(gè)會(huì)議,因?yàn)樵诖酥八谎?qǐng)參加了在京文化界人士一次類(lèi)似的會(huì)議,。而通知醴陵瓷業(yè)派代表參加這次會(huì)議就是他提議的,。當(dāng)他聽(tīng)我們介紹醴陵瓷業(yè)在會(huì)上承擔(dān)了十大建筑的日用、藝術(shù)瓷的任務(wù)時(shí),,他顯得格外高興,。一邊聽(tīng)我們介紹,一邊抽條凳子從柜頂上隨手取出明清古瓷在地上擺了一大堆(大大小小的花瓶、盤(pán)碗和罐子等共30多件),,毫無(wú)保留地讓我們?nèi)慷紟Щ靥沾裳芯克鞴ぷ髦械膮⒖?。這次倉(cāng)促拜訪,又親切敘談近兩個(gè)小時(shí),,我們無(wú)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(zhì)上都獲得巨大的收獲,。此后幾十年,我們常有書(shū)信往來(lái),,主要是向沈老請(qǐng)教的事情多,,我有機(jī)會(huì)去北京開(kāi)會(huì)又去看望過(guò)他幾次,與我同伴去看望他的,,除前面說(shuō)的唐漢初老藝人(已故)外,,還有陶瓷研究所青年畫(huà)師肖石泉、情報(bào)室主任賈杰民(90年代曾任陶瓷研究所所長(zhǎng)),,現(xiàn)均退休,。
1959年醴陵陶瓷研究所還承擔(dān)了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用的東漢科學(xué)家、天文學(xué)家,、 文學(xué)家張衡(公元78年-139年)的塑像研制,。擔(dān)任此一重要塑造任務(wù)的陶瓷研究所青年雕塑工作者羅景炘(1954年中南美專(zhuān)畢業(yè)),對(duì)東漢時(shí)期士大夫階層又是朝廷命官,、兩度擔(dān)任宮廷執(zhí)掌天文的太史令這樣的人應(yīng)穿戴什么衣冠,,其儀表如何表現(xiàn)頗多思量。我想起了沈從文先生,,他那時(shí)在故宮工作,,對(duì)古代服飾很有研究,隨即向沈老寫(xiě)了一封請(qǐng)教的信,,并由羅景炘同志持我的信專(zhuān)程去了一趟北京,。這里順便說(shuō)點(diǎn)插曲:還是1963年的時(shí)候,周總理在一次會(huì)議上向當(dāng)時(shí)文化部副部長(zhǎng)齊燕銘提出,,許多國(guó)家都有服裝博物館,,他說(shuō)中國(guó)幾千年文明史,就是沒(méi)有服裝史的專(zhuān)著,。齊當(dāng)即向周總理推薦,,這件事沈從文可以搞,總理也知道沈從文的才能,,當(dāng)時(shí)就當(dāng)機(jī)立斷說(shuō):“好,這事就請(qǐng)沈從文來(lái)做,,一定會(huì)做好,。”沈從文在新中國(guó)成立后一直在故宮工作,他從此改行研究青銅器,、陶瓷器,、漆器、玉器及古代服裝等,,十多年下來(lái),,他在文物史方面幾乎成了“富甲天下”的專(zhuān)家了。這次在接受周總理的囑托后,,他更是全身心傾注在古代服飾的研究上,。沈從文先生前后費(fèi)了18年心血(其中“文革”干擾了若干年),一本包括400張彩色圖像,、20多萬(wàn)文字說(shuō)明的《中國(guó)古代服飾研究》的大型著作,,終于在他八十高齡的1981年出版問(wèn)世了,在國(guó)內(nèi)外引起了強(qiáng)烈的反響,。這部巨著對(duì)于我國(guó)從商朝到清朝3000多年間,,各朝代各階層的服裝進(jìn)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與探索,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文化,,填補(bǔ)了我國(guó)物質(zhì)文化史上的一項(xiàng)空白,,對(duì)沈老來(lái)說(shuō)特別是完成了周總理的遺愿,他內(nèi)心是多么高興自不待說(shuō),。

前面提到的羅景炘同志持我的信到故宮拜訪了沈從文先生,,當(dāng)然又得到了沈從文先生的熱情接待和指導(dǎo),不僅張衡的衣冠裝束問(wèn)題得到了解決,,沈從文先生還向羅景炘提出了塑造張衡像應(yīng)注意的儀態(tài)和為人氣質(zhì),。有了這樣難得而又熱心的指導(dǎo)幫助,羅景炘的創(chuàng)作活動(dòng)如魚(yú)得水,,很快就順利完成了任務(wù),。古銅色的張衡塑像(1.4米高)從歷史博物館 1959 年國(guó)慶10周年開(kāi)館起一直陳列在該館反映東漢時(shí)期的顯要位置上,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包括羅景炘及為完成此一塑造任務(wù)的有關(guān)人員由此為首都的歷史博物館順利展出作出了應(yīng)有的貢獻(xiàn),。
沈從文對(duì)醴陵瓷業(yè)的發(fā)展,,對(duì)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工作上的幫助是很大的。筆者曾在《湖南日?qǐng)?bào)》(1988年10月8日),、《醴陵文學(xué)》(2000年第4期)分別發(fā)表了《憶沈從文》和《沈從文和醴陵瓷》兩篇拙文,。其中介紹了沈從文先生為建議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籌建“陶瓷館”(即今湖南陶瓷陳列館,位于醴陵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內(nèi)——編者注)一些具體意見(jiàn)的親筆信,。沈老慣用毛邊宣紙,,采用毛筆豎行,蠅頭小草,,似行云流水,,筆者無(wú)意“借信掠美”,,發(fā)表這封信只是可以看到沈老對(duì)醴陵瓷業(yè)的傾心關(guān)注。
沈從文先生原信(節(jié)選):
李所長(zhǎng),,前信想已收到,。我這里曾為省博李昌鄂同志寫(xiě)了封信,問(wèn)他省博方面領(lǐng)導(dǎo)同志是否還知道十多年前,,故宮撥調(diào)的瓷器,,主要設(shè)想是為協(xié)助醴陵瓷生產(chǎn)的參考,便于改進(jìn)和提高在外銷(xiāo)上既打“經(jīng)濟(jì)仗”又打“文化仗”,。若新領(lǐng)導(dǎo)明白后,,即一時(shí)不能調(diào)幾十件有用名瓷給研究所,也應(yīng)為研究所特別勻出個(gè)房間,,讓你們就生產(chǎn)需要臨摹個(gè)百十件樣子供參考,,最好還是能同意輪流調(diào)一部分到瓷研所去,才不失本意,。你們?nèi)粜枰?,交涉又有周折,我可向李振軍(時(shí)任湖南省委副書(shū)記——編者注)寫(xiě)封信,,談?wù)勥@件事,。其次,我還曾為收了一批外產(chǎn)日用刻玻璃,,有極好的,,不知是否還保存在省博,或是展覽館庫(kù)房中,,當(dāng)時(shí)用意是“洋為中用”,,搞玻璃不能不學(xué)外來(lái)物。與其凍結(jié)在庫(kù)房中,,不如也撥給瓷研所,,為改進(jìn)醴陵日用玻璃參考。僅僅這個(gè)外來(lái)的不夠,,還可設(shè)法搞百十件各省的,,歷博也有不少。新出土的唐宋元明金石器盤(pán),、碗,、壺、罐造像,,并已畫(huà)出的圖樣,,就可兩結(jié)合,搞出嶄新造型和花紙新的生產(chǎn),,在世界上也是會(huì)得到藝術(shù)上的成功,。
(本文原載于《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史料》)